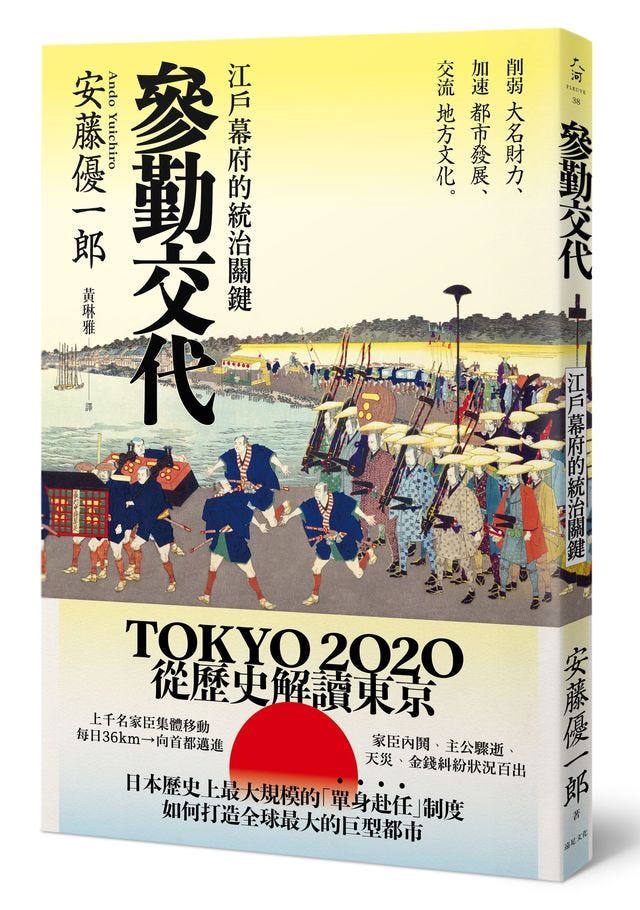消逝的生命與關不住的監情:網走監獄博物館

我沒有在網走站前等路線巴士,而是利用導航,徒步走了兩個公車站點之後,在「刑務所前」的站牌上車,刑務所當然就是網走現在的監獄,跟天都山的監獄博物館是兩個不同的地方。正值周末,目測車上的乘客,應該都是要前往博物館,果不其然,到站之後,全員下車一個不剩。
在其他城市,博物館或許不是遊客的「必去」選項,不過,來到網走,除了破冰船,監獄博物館則是遊人大多不會錯過的景點。畢竟,參觀以監獄為主題的博物館,在日本是難得的獵奇體驗。才進入園區,就跟樹叢裡栗鼠打了個照面,然後,牠就越獄了,而我的監獄之旅才正要開始。從窗口拿到一張近千塊的門票走進獄門關,頓時仍躊躇著要從哪開始看起。
1840年代,現代的監獄制度開始在西方逐漸成形、發展,取代以往的公開處刑,被視為一種以「人道」改造罪犯的制度。傅柯的經典名著《監視與懲罰:監獄的誕生》,就是在討論18世紀以降,西方監獄制度的誕生過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