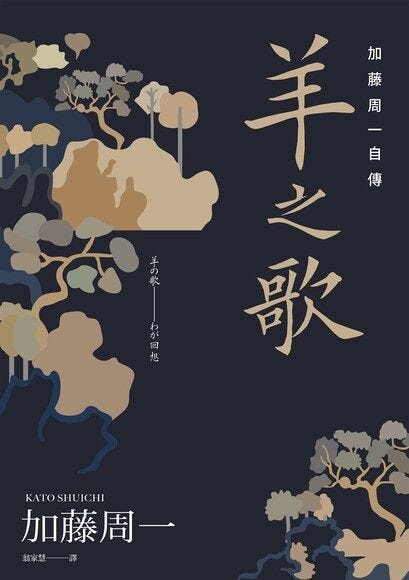数羊数了很久:我读《羊之歌:加藤周一自传》
2021年3月初,笔者收到麦田出版社的行销团队,寄赠的这本《羊之歌:加藤周一自传》,谨以此拙文致谢。
尽管书中已有作家邱振瑞先生的导读,以简洁的篇幅介绍了作者行医从文的历程,以及在反安保、反战与军国主义的批判立场。读毕本书,基于个人的职业病,又去翻阅了作者的其他作品,包括他在1960年代为「每日新闻社」撰写,其后增删并出版,并重刷过多次单行本的《世界漫游记》。
羊年出生的加藤周一,以《羊之歌》作为其散文体自传的书名,将1960年代中叶连载于《朝日周刊》的一系列文章为基础,集结为《羊之歌》与《续羊之歌》,在1968年出版成书。今年发行的繁中版本,所收录者即为正续两集的内容。
羊的温驯,或许使人联想到羊群,群聚并遵行一致的方向行进,代表合群、从众。而离群的羊,往往也意味著失去群体的庇护,容易陷入被掠食、吞噬的危险。
1931年,加藤周一进入当时的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校就读,在他入学的几个月前,发生了满州事变,暴走的军国主义,自此将日本推入了战争的不归路。而二二六事件、芦沟桥事变,与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,则在他入学高校期间陆续登场。1940年,加藤周一开始就读东京帝大医学部,次年,太平洋战争爆发,1944年,盟军开始对强弩之末的日本,展开了本土空袭行动。
中学校时期,他流连于父亲的书房,阅读《万叶集》,引领其进入诗歌文学的奥妙与魅力,为他其开启一扇想像世界的大门;与此同时,启发他洞察日本近代国家本质,理解自身面对现实生活的沉闷与束手无策,则是芥川龙之介的著作。
高校时期,结识中村真一郎等诸多文学同好,触发了他对歌舞伎、能、狂言,与西方文学思想的兴趣,他亦曾加入映画演剧研究会,也曾担任过文艺部委员。东大医学部时期,他大量涉猎西方思想与文学,希冀借以反思人的存在。
在举国陷入军国主义狂潮,与大东亚共荣想像的年代,少年加藤周一,则作为一只离群的羊,通过文学的读写,与社交网路中,寻觅出另一条出路,形塑了他日后的批判军国主义,捍卫民主与和平宪法的反战立场。
加藤周一以文学作为志业,使其具备独立批判的思想资源之外,或许也有来自原生家庭潜在的影响。例如加藤周一在书中提到,任职大学医局长的父亲,教授的候选人推荐问题上与校方意见相左,遂从大学医院离职,成为自行开业的医生,仰赖少数上门求诊的患者,与为名人富户定期出诊,以维持四口之家的生计。
选择与多数人的一致思想或行动保持距离,向来不是容易的事。
阅读一代日本文学评论大家,回顾自身优游涵泳于医学与文学的历程,及战后选择参与反战的思想脉络之外,从这部自传也能俯拾许多大正、昭和时期的生活史料,例如加藤周一的旅行经验。
随父母前往埼玉县熊谷的老家省亲,是加藤周一儿时最期盼的旅行。从涩谷出发到上野车站,抵达熊谷,数段辗转移动的路程,与乡间的小住数日,对加藤周一而言,是脱离东京城市日常空间,及人间关系的解放时刻,这样的距离感,也是他思索城乡生活,与作为「旁观者」身分的开端。
当火车通过荒川铁桥,车轮转动的节奏与汽笛的声响,对加藤周一来说,是暂别东京的意象,与对终点站的期待。农村的稻田、林间、草泥香气与鸟鸣,与乡野小路间的信步或奔驰,是在东京少有的体验。
另一方面,农村孩童熟门熟路的在小路间穿梭,时隐时现,与对他这个「东京人」的好奇,让他意识到自己即使渴望成为此地的一份子,在地方孩童的视线中,仍旧是个「东京人」。
明治以降,旅日外国人在日本国内的山间海边,兴建别墅躲避暑热,渐成一种新兴的休旅风气。时序进入大正、昭和时代,避暑休旅之风,也逐渐普及在本国人之间。高端的富裕层,多仿效早期外国人的习惯,盖起避暑别墅;中产家庭则会以租赁的方式,承租该地的房舍,作为避暑休旅的居所,宿泊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月。
加藤周一在就读中学与高校时期的1930年代,每年夏休在信浓高原追分村的避暑生活,就是源于上述的旅行文化背景。位于轻井泽外围的追分村,在江户时期是中山道(或称中仙道)上著名的宿场,参勤交代停止之后,没落许久的旅笼屋,从轻井泽蜕变成著名的避暑地过程中,获得转型重生的商机,吸纳了大批人群从东京前来的休旅的住宿需求。此外,追分村当地的寺院,也会在夏季提供短期出租的单间雅房给学生居住。
加藤自传中提及追分村的「油屋」,现已由旧址移转,改建成保留原样的「油やSTAY」日式旅馆。昭和时期的「油屋」,曾是许多名人来此避暑时的居所,写作《风起》(风立ちぬ)的小说家崛辰雄,就曾是这里的住客。
追分村的林间雾霭,变化莫测的浅间山景,绿草与火山灰小径和白桦树,与为了避暑在此离返的人群,少年加藤周一在信浓的高原牧歌中,体悟到借由远离东京,再重新认识东京的旅行意义。
加藤周一那位早年游欧,军旅退伍后经商,多金且作风洋派的外祖父,是他儿时最初接触西方事物的媒介。外祖父在银座经营义大利餐厅,拥有气派的洋房,陈列著各种购自外国的纪念品,亦能操一口流利的法语。
战后作为半公费生,负笈欧洲的加藤周一,初次抵欧,自承有种与童年世界久别重逢之感。以往外祖父引领其接触的西洋器物、饮食、音乐和法语,也让加藤周一在初抵西欧之际的旅行视线所见,并非是千里跋涉的实际异域,而是长假之后的旧地重返。
儿时的西洋印象,在此后海外与日本之间往返与旅居的生涯中,逐渐退为加藤周一实际认识的西洋图景里,极为渺小的一小部分。
日本在战后从废墟中重新站起,直至1964年全面开放国人自由赴海外旅行之前,若非公门、商务或留学的需要,能够出国者可谓凤毛麟角。在自传中,加藤周一书写其1950年代的去国远行,搭乘著当时仍非普及交通工具的飞机。
加藤周一的空路移动经验,并未如同时期取道昔日「帝国航路」赴欧的远藤周作等人,自身作为战败国民,在旅路上强烈感受到各地的仇日的情绪。从羽田机场辗转中停香港、喀拉蚩、贝鲁特等城市,辗转在巴黎降落,加藤周一由此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学业、工作与世界行旅。
求学于巴黎大学医学院,法语是加藤周一深造学术与日常沟通的语言;为日籍游客与会议担任翻译,母语是糊口的工具,切换著不同的语言,习惯从任何事对比东京与巴黎,欧洲各国的旅行足迹所至,亦处处留心,观照日欧文化艺术的本质。
加藤周一在自传中,叙述其文学、文艺的学养与知识系谱,并非笔者能力所能评述,仅就其传中的部分旅行书写段落,浅述自身阅读之所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