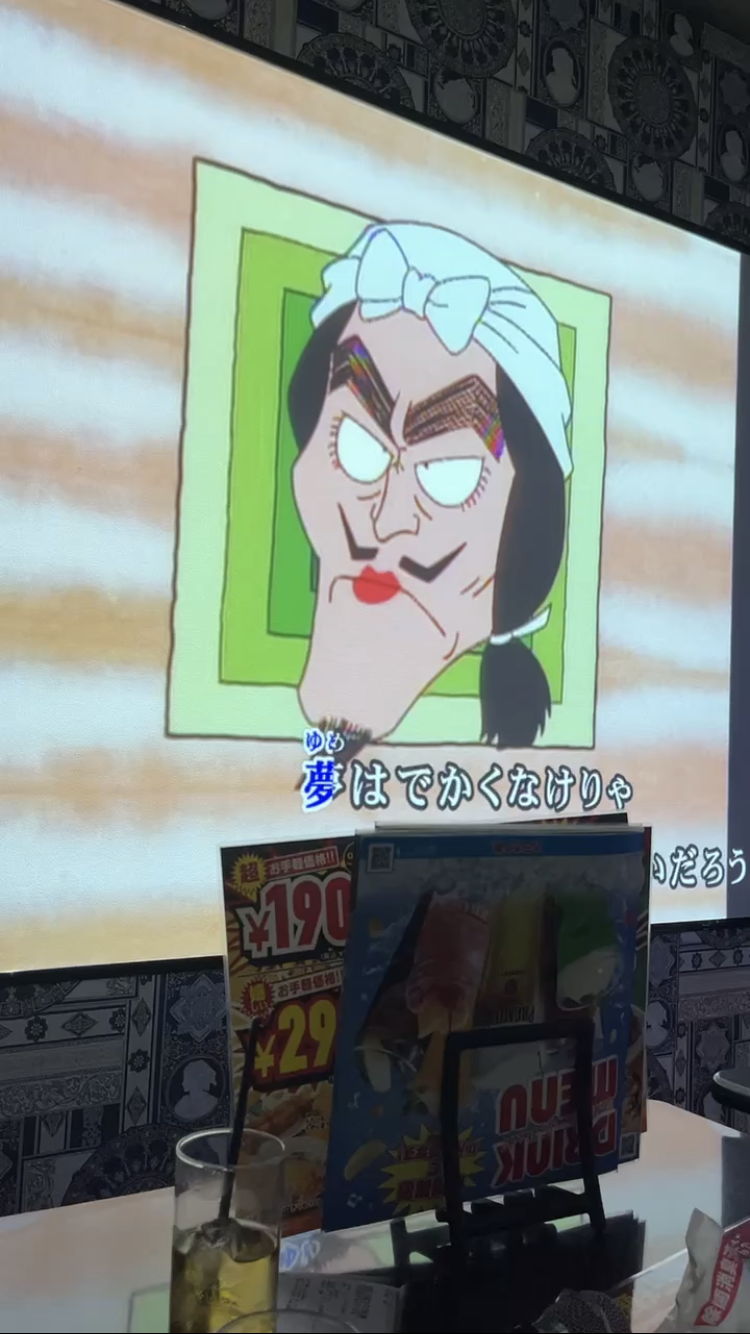終電後的上野,意外地看見了日本人的男兒淚
在東京和一個靜岡的朋友見面時,沒想到她會約我去上野,我一直以為那裡是遊客的據地,當地人可能更偏好其他地方。
吃完第一攤,按照我們的文化,少不了續攤。時間不過十點多,走出居酒屋以後,橫街的熱鬧程度已經減半,與想像中的夜生活出現落差。隨便找了間居酒屋坐下,裡面只有兩三桌客人,與方才的坐無虛席形成強烈對比。坐了大概一小時,我們準備起身結帳離去時,一直坐在我們後面的那枱客人忽然問我們要不要一起玩。我腦海裡面第一個疑問是,他們沒有聽到我們是用韓文在聊天嗎。我朋友用日文跟他們說,我是外國人,一個男人沖著我露出一個微笑,說:「English,Ok!」我笑了笑,轉身問我朋友想不想去,她說有點無聊,不如去玩一玩。於是順利成章,我們兩桌人就往外移動,去了另一家居酒屋繼續續攤。
坐下後,發現日本人的英文真的是有限公司,比起我快要忘光的日文來得更差,聽得我一頭霧水。轉念一想,不如我用蹩腳的日文跟他們交談還來得方便,反正聽著頭痛的人是他們不是我。反倒是這樣,整桌都一致地用日文聊天更為方便。言談之間,我知道矮一點的那個男生原來是奈良人,和好多人一樣,上京追尋自己的夢想,在一家電視台工作,閒時會到距離東京不遠的湘南海岸滑水,觀摩一眾高手。不過來了幾年,終究發現東京並不是一般人能待下去的地方,從有夢想到迷惘,現在打算放棄這邊的五光十色,回去那個滿街小鹿的故鄉,而啟程日子正好就是明天。
聊著聊著,很快就到了十二點多,是日本電車很多末班車開出的時間。我和朋友查了一下,我們的末班車就在12點46分。在日本,錯過末班班好像是一件大事,可能會招不到計程車,也有些人在網吧過夜。反正,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植根在我的認知裡。我切換到熟悉的韓文問朋友:「我們應該差不多起身離開了吧,這裡走去車站也有一些距離。」兩個男生是懂得看氣氛的人,馬上就察覺到我們要離開,於是又設法叫我們多玩一會,保證我們能夠安全歸去。我好奇另一個高的男生是不是第二天會放假,不然怎麼可能會想要續攤,他卻說,自己六點就要起來準備上班。
在我們猶豫的時間裡,末班車已經悄然無息地開走了。想著現在走和晚一點走,其實也沒差,於是又離開了居酒屋,尋找下一個落腳地。終電過後的上野,街上一片冷清,店鋪已經打烊,遊人和上班族也啟程回家,街上還有亮著燈的店只有零星幾家居酒屋、便利店,以及卡拉OK。一月的街頭,凌晨寒風刺骨,不許容我們多想,於是直接進了一家卡拉OK。
兩個日本人挺好客,問我有沒有哪首歌想點,不要說日文,其實我連韓文歌都不太會,無謂獻醜,把咪高峰交給他們。不過,高個子說:「你聽過的歌都可以點,讓我們幫你唱。」於是我腦海裡浮現了《忍者亂太郎》的勇氣100%。接下來,不知怎的,就變成了我點歌,他們唱歌,我點了好多首日文的經典,或者那些有改編成廣東歌的歌曲,譬如雪之華。
後來也不止是我點的歌,他們也點了一些自己的飲歌,向我介紹那是一些日本上個年代耳熟能詳的歌。我說我也懂一首上個年代耳熟能詳的歌。高個子男生問我是什麼,我說是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。他甚是共嗚地向我舉起大拇指,分秒之間就點了那首歌。矮個子的男生唱了兩句之後,開始哽咽,說自己唱不下去。我朋友問為什麼,他說:「我明天就要和這個朋友分開,我真的好傷心。」說畢,就掩著臉擦著眼淚。我想著他是不是被剛才歌詞裡的那句「明天的此刻,我一定哭泣著」刺痛了。高個子的男生也湧上一陣感性,說他這樣一哭,他也很想哭。結果兩個大男人就在現場聽著First Love作背景音樂,流著眼淚。我開玩笑的問,他們是不是在交往,朋友就給他們遞紙巾。矮個子邊擦眼淚邊說,他一個人到異鄉打拼,最幸運就是遇到這個朋友,在陌生的環境裡,支持著他繼續撐下去。高個子也徐徐透露自己的心聲,他說他不想這一夜結束,因為一覺醒來,大家就要分開。到了這個時間點,我開始懂他們兩個為什麼那麼想續攤。
凌晨快要四點,即便他們的友誼多讓人感動,我的精力已經追不上,於是我和我朋友就退場。他們把我們送到門口,可能因為上野真的沒人,在門口就有一輛計程車,沒有上映印象中的那些場景。朋友讓我先上車回去,高個子男生向我塞了幾千日元,說想幫我付計程車的費用,謝謝我們陪他們度過最後一個晚上。幾個人好像醉了一樣,向計程車司機叮嚀我是外國人,請安全送我回去,然後對著車子一直揮手,直到我的車子遠去。
我看著車窗外掠過的寂靜,回想起這一夜的經歷,這個日本,我大概不會有機會再體驗第二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