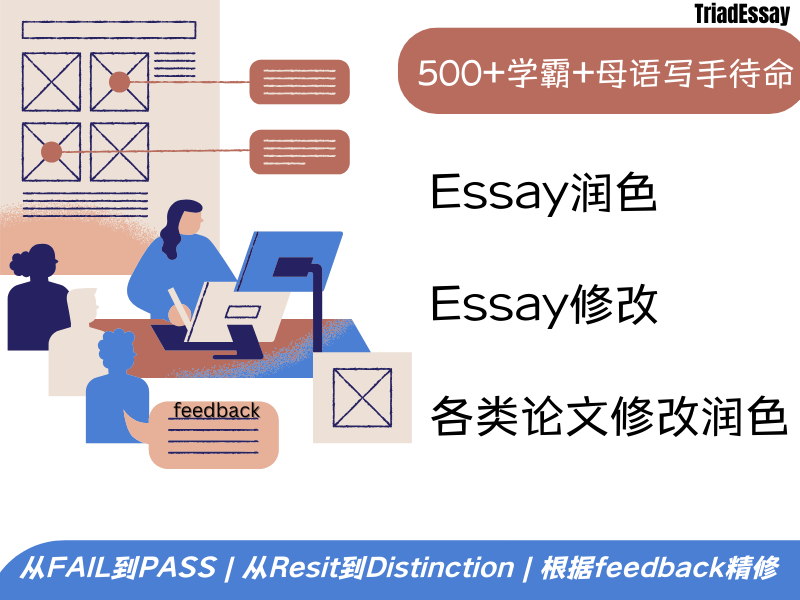学术无界:一种被体面遮蔽的失真
很多人谈到“学术”时,下意识会把它与秩序、理性和进步联系在一起。它似乎天然地站在道德高地上:以证据说话、以理服人、不掺杂情绪。也正因为如此,学术常被视为一种比日常世界更“干净”的存在。可一旦你真正靠近这个系统,参与其中的运作,就会发现它远没有想象中那样超然。
我第一次对这种落差产生明确感受,并不是在读论文时,而是在一次与研究毫无关系的场合。那是一次评职称相关的内部讨论,几位资历不浅的老师围坐在会议室里,桌上摆着候选人的材料。讨论并没有围绕研究内容展开多久,很快就转向了期刊等级、影响因子、署名顺序,以及“这个人是不是我们圈子的”。有人半开玩笑地说:“文章其实也就那样,但人挺聪明的。”这句话没有被质疑,反而像一种默认共识。
那一刻我意识到,所谓“以学术标准评判”,很多时候并不是在评判理解深度,而是在确认一种身份。聪明、潜力、智识感,这些模糊却安全的词汇,往往比清楚解释研究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更重要。
从那之后,我开始更留意学术人员说话的方式。在会议上、在答辩中、在非正式讨论里,很多人习惯用一种高度抽象、去情境化的语言交流。他们讨论“理论贡献”“方法创新”,却极少触及这些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具体连接。仿佛一旦谈到真实情境,学术的纯度就会被稀释。
这种姿态并非偶然,它与学术体系中根深蒂固的 meritocracy 信仰密切相关。能力被假定为可被客观衡量,智识被视为一种可以排序的属性。在这样的逻辑下,情绪、经验、个人背景都被认为是“噪音”。而越是能够表现出冷静、抽离和高度概括的人,就越接近“合格学者”的形象。这跟类似于 triadessay 等代写机构说的非常像。
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许多学术人员并非真的与现实无关,而是学会了在公共场合隐藏这种关联。他们在私下里对制度的不公、评审的随意、资源分配的倾斜心知肚明,却在正式写作中继续维护一种“系统理性”的叙事。这种分裂久而久之,会演变成一种伪善——不是因为他们有意欺骗,而是因为承认系统的荒谬,会动摇他们自身位置的正当性。
我曾听一位年轻学者在酒后抱怨,自己花了三年时间做的研究被审稿人用一句“interesting but limited contribution”打发。他说这句话时情绪很重,但第二天在学院的公开场合,他仍然用同样的语言评价他人的工作。那一刻我意识到,学术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,更是一种自我驯化的机制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学术无界”才显得必要。它并不是要否定智识或反对能力,而是拒绝把 intelligence 当成一种道德资本。在无界的状态下,理解比聪明更重要,诚实比优雅更重要。你可以承认自己不懂,可以在表达中留下犹豫,而不是急于给出一个听起来“学术”的答案。
这种状态往往出现在体系边缘。比如跨学科合作中,那些尚未掌握彼此术语的人,被迫用更朴素的语言解释问题;又或者是在与非学术背景的人交流时,你突然发现自己必须回答一个简单却尖锐的问题:这项研究到底有什么用?在这些时刻,学术的防护层会被暂时剥离。
然而,这样的交流在正式学术空间中并不被鼓励。因为它暴露了不确定性,也削弱了权威感。而权威,恰恰是精英主义得以维持的重要资源。只要“懂的人自然懂”仍然是默认逻辑,那么学术就可以继续远离普通经验,而无需为此负责。
学术人员的 detachment,并不只是情感上的冷漠,更是一种结构性距离。他们被训练去分析问题,却很少被鼓励参与问题;被奖励提出框架,却不需要承担后果。这种分工在制度层面是合理的,但一旦成为习惯,就会让学术逐渐失去与现实的触感。
学术无界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,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暂时的逃逸路径。在那里,你可以不急着证明自己聪明,不必每一句话都指向发表潜力。你可以把理解当作过程,而不是资本。这种状态不体面,也不高效,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专业,但它保留了一种被学术体系不断挤压的可能性:真实的沟通。
也许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学术是否需要秩序,而是它是否还能容忍那些不完全服从秩序的时刻。毕竟,如果一个以理解世界为目标的实践,最终只能与现实保持安全距离,那么它的精致,很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空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