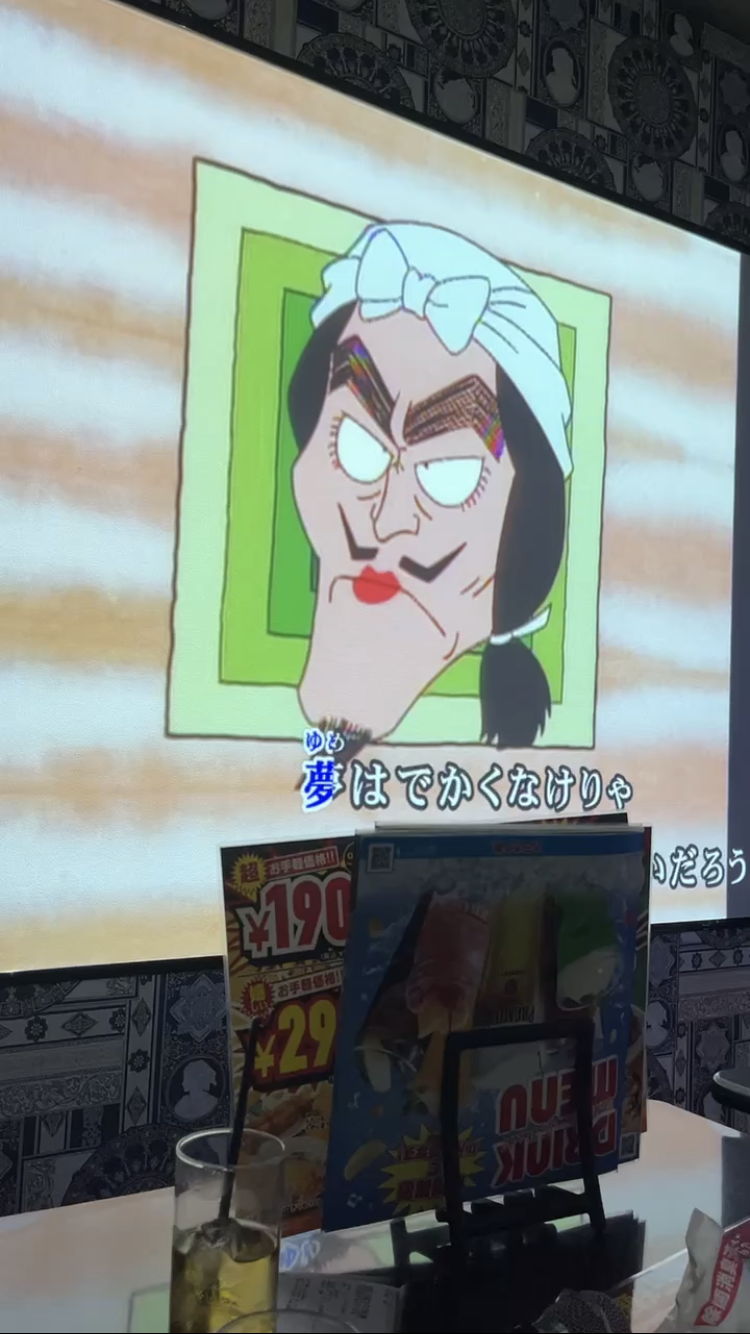终电后的上野,意外地看见了日本人的男儿泪
在东京和一个静冈的朋友见面时,没想到她会约我去上野,我一直以为那里是游客的据地,当地人可能更偏好其他地方。
吃完第一摊,按照我们的文化,少不了续摊。时间不过十点多,走出居酒屋以后,横街的热闹程度已经减半,与想像中的夜生活出现落差。随便找了间居酒屋坐下,里面只有两三桌客人,与方才的坐无虚席形成强烈对比。坐了大概一小时,我们准备起身结帐离去时,一直坐在我们后面的那枱客人忽然问我们要不要一起玩。我脑海里面第一个疑问是,他们没有听到我们是用韩文在聊天吗。我朋友用日文跟他们说,我是外国人,一个男人冲著我露出一个微笑,说:「English,Ok!」我笑了笑,转身问我朋友想不想去,她说有点无聊,不如去玩一玩。于是顺利成章,我们两桌人就往外移动,去了另一家居酒屋继续续摊。
坐下后,发现日本人的英文真的是有限公司,比起我快要忘光的日文来得更差,听得我一头雾水。转念一想,不如我用蹩脚的日文跟他们交谈还来得方便,反正听著头痛的人是他们不是我。反倒是这样,整桌都一致地用日文聊天更为方便。言谈之间,我知道矮一点的那个男生原来是奈良人,和好多人一样,上京追寻自己的梦想,在一家电视台工作,闲时会到距离东京不远的湘南海岸滑水,观摩一众高手。不过来了几年,终究发现东京并不是一般人能待下去的地方,从有梦想到迷惘,现在打算放弃这边的五光十色,回去那个满街小鹿的故乡,而启程日子正好就是明天。
聊著聊著,很快就到了十二点多,是日本电车很多末班车开出的时间。我和朋友查了一下,我们的末班车就在12点46分。在日本,错过末班班好像是一件大事,可能会招不到计程车,也有些人在网吧过夜。反正,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植根在我的认知里。我切换到熟悉的韩文问朋友:「我们应该差不多起身离开了吧,这里走去车站也有一些距离。」两个男生是懂得看气氛的人,马上就察觉到我们要离开,于是又设法叫我们多玩一会,保证我们能够安全归去。我好奇另一个高的男生是不是第二天会放假,不然怎么可能会想要续摊,他却说,自己六点就要起来准备上班。
在我们犹豫的时间里,末班车已经悄然无息地开走了。想著现在走和晚一点走,其实也没差,于是又离开了居酒屋,寻找下一个落脚地。终电过后的上野,街上一片冷清,店铺已经打烊,游人和上班族也启程回家,街上还有亮著灯的店只有零星几家居酒屋、便利店,以及卡拉OK。一月的街头,凌晨寒风刺骨,不许容我们多想,于是直接进了一家卡拉OK。
两个日本人挺好客,问我有没有哪首歌想点,不要说日文,其实我连韩文歌都不太会,无谓献丑,把咪高峰交给他们。不过,高个子说:「你听过的歌都可以点,让我们帮你唱。」于是我脑海里浮现了《忍者乱太郎》的勇气100%。接下来,不知怎的,就变成了我点歌,他们唱歌,我点了好多首日文的经典,或者那些有改编成广东歌的歌曲,譬如雪之华。
后来也不止是我点的歌,他们也点了一些自己的饮歌,向我介绍那是一些日本上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歌。我说我也懂一首上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歌。高个子男生问我是什么,我说是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。他甚是共呜地向我举起大拇指,分秒之间就点了那首歌。矮个子的男生唱了两句之后,开始哽咽,说自己唱不下去。我朋友问为什么,他说:「我明天就要和这个朋友分开,我真的好伤心。」说毕,就掩著脸擦著眼泪。我想著他是不是被刚才歌词里的那句「明天的此刻,我一定哭泣著」刺痛了。高个子的男生也涌上一阵感性,说他这样一哭,他也很想哭。结果两个大男人就在现场听著First Love作背景音乐,流著眼泪。我开玩笑的问,他们是不是在交往,朋友就给他们递纸巾。矮个子边擦眼泪边说,他一个人到异乡打拼,最幸运就是遇到这个朋友,在陌生的环境里,支持著他继续撑下去。高个子也徐徐透露自己的心声,他说他不想这一夜结束,因为一觉醒来,大家就要分开。到了这个时间点,我开始懂他们两个为什么那么想续摊。
凌晨快要四点,即便他们的友谊多让人感动,我的精力已经追不上,于是我和我朋友就退场。他们把我们送到门口,可能因为上野真的没人,在门口就有一辆计程车,没有上映印象中的那些场景。朋友让我先上车回去,高个子男生向我塞了几千日元,说想帮我付计程车的费用,谢谢我们陪他们度过最后一个晚上。几个人好像醉了一样,向计程车司机叮咛我是外国人,请安全送我回去,然后对著车子一直挥手,直到我的车子远去。
我看著车窗外掠过的寂静,回想起这一夜的经历,这个日本,我大概不会有机会再体验第二次。